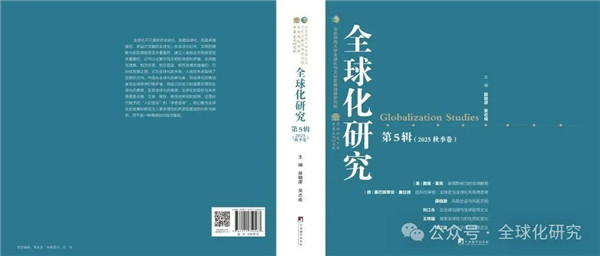王辉耀:探索全球权力的性质和变化——纪念“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
全球化研究 | 2026年1月13日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外交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其60余年的学术与公共服务生涯中,与罗伯特·基欧汉共同创立国际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提出“软实力”“巧实力”等核心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权力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他曾两度任职美国政府高层,参与核不扩散、亚洲权力平衡及美日同盟政策实践,并通过跨国智库和公共外交推动国际交流。笔者亦基于与奈的多年交流,深入理解其软实力理论在中美关系中的实践与应用。奈的理论与实践遗产为理解21世纪国际秩序、全球权力转移及中美竞合关系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约瑟夫·奈 软实力 巧实力 中美关系
惊悉“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于当地时间5月6日去世,享年88岁。奈被誉为“软实力之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共同创立了国际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理论,发展了“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等重要概念。与此同时,奈又两度进入美国政府高层实践其理念,成为横跨学界和政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学术遗产和政治遗产都对当前世界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7.1.19—2025.5.6
我和约瑟夫·奈教授交往多年,多次与他交流对话。他曾表示:“美中之间有共同利益,应该开展合作,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如果两国展开合作,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就会发生改变。”他的去世,是国际战略界和国际关系界的一大损失。
自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以来,已经过去了34年。我们已然见证了世界格局从“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2024年,中美两国GDP总额超过4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超过43%。我们还见证了全球权力正在发生历史性大转移:从西方转向东方——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代表,中国则被视为亚洲复兴的核心。奈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使从西方向东方的权力转移以一种惠及所有国家的形式实现,而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大国竞争? ”毋庸置疑,此处的“大国竞争”指的是中美关系。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处理得好则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处理不好则殃及全球。这个问题也是我与奈教授相识相交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
奈教授的一生可谓是“美国世纪”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生于1937年,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世纪”正式开启。彼时经济份额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美国,一片欣欣向荣,处处都是上升机会。奈的祖辈都是移民,他在新泽西州乡村长大,父亲是一名债券公司合伙人,母亲是一名秘书。他在家乡的小学和中学接受教育,凭借自身努力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又在牛津大学(获得罗德学者奖学金)和哈佛大学深造,师从亨利·基辛格等知名学者。他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都曾在英国留学,具有广泛的国际视野。奈在哈佛执教几十年,发展了“软实力”“巧实力”和“新自由主义”等重要概念。
奈与罗伯特·基欧汉共同创立了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可以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他们则提出经济相互依存还可以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或武器。奈与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应该用现实主义视角从世界没有全球政府、国家之间靠权力制衡的现实入手。他们1976年成书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后经不断再版,至今仍然作为国际关系教材使用。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再度甚嚣尘上。奈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分析了大量的材料,认为一国的实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军事这些硬实力(hard power)。为了驳斥“美国衰落”的观点,奈开始写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在书中,奈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在同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发表同名论文。这一开创性理论将国家权力解构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维度:前者涵盖经济规模、军事力量与科技水平等可量化资源,后者则指向文化传播、价值认同与外交策略等柔性影响力。奈强调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形成“巧实力”,才能实现国家战略效能最大化。凭借这一理论体系的持续建构,奈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软实力之父”。2004年,奈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文化吸引力与制度认同在全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2020年,奈在《道德重要吗? ——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一书中另辟蹊径,以“道德维度”为分析框架,通过考察从罗斯福到特朗普时期的外交决策,为解读美国全球战略演变及当代国际格局变迁提供了创新视角。该书既延续了其软实力理论的核心关切,又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伦理向度。奈对国际关系中权力本质的剖析和理论思想影响了几代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2011年,奈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
学而优则仕。除了在哈佛大学从教,奈还曾两度在政府任职。在卡特政府时期,奈担任助理国务卿,参与提出并大力推动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计划,并在任内致力于防止核扩散政策的落实,这对我们当前世界的核安全仍具有重要意义,奈也因此获得美国国务院杰出服务奖章。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奈先后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发起《奈氏倡议》(Nye Initiative)重新加强美日同盟,在亚洲维持权力平衡,因其卓越贡献,他获颁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奖章和国防部杰出服务奖章。
进入21世纪,奈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两重大型权力转移。一是“横向”转移,即权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欧洲和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二是“纵向”转移,即权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行为体,因为许多跨越国界的挑战已非一国政府能够单独应对,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行为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权力平衡,并避免这种调整导致灾难性后果,对于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是以,晚年的奈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些问题。
二
我和奈教授相识于2010年,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而奈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前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奈推动建立了许多中美交流项目,在卸任后也积极参与此类活动。他给我们做讲座,当时他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总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此后一直保持着深度交流。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奈教授给我的印象是聪敏睿智、视野宏大、极富远见,并且平易近人。即使在退休后,奈教授仍然密切关注美国与世界的变化,持续发表高水准的国际政治评论文章,并多次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多地参加重要活动和主持会议,其中包括慕尼黑安全会议。他也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保持着广泛的公共影响力。此外,他还在阿斯彭战略集团(Aspen Strategy Group)、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等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中任职,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与奈教授交往的这些年中,他总是亲自回复我的每一封邮件,多次与我对话,始终表现得平易近人,这令我深受感动。
与奈教授初相识时,中美关系尚处于较为良好的阶段。彼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受“9·11”事件影响,聚焦于打击恐怖主义并以中东地区为重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刚满十周年,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与美国通力合作应对危机、促进全球复苏。奈教授以国际政治学者的敏锐性,早在十余年前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崛起进程,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写道,“中国崛起”这一表述并不恰当,“复兴”会更为准确。此后,他多次发表文章论述中国软实力,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及来华留学生人数和外国游客人数的大幅增长。同时,中国GDP增加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倍,对外经济援助和开放市场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国际吸引力,但奈教授也指出,“中国的软实力同样有很长的路要走”。2009年,他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基础也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截然不同,并首次论述了中美软实力的互动,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为了抗衡美国的软实力”,“那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势必会挑战西方模式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无须将中美之间的软实力互动视为一种竞争,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更加复杂的竞合关系”。
2012年,奈教授来华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软实力的报告,他在演讲中谦逊地说,虽然“软实力”概念是自己在20多年前才提出的,但其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且被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老子所谓“太上,不知有之”便包含着发挥软实力的意蕴,足见其源远流长。他谈到,软实力并非美国所独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儒家思想重视社会和谐、礼、孝和恻隐之心,这些价值观影响了东亚大部分地区,而且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撰述的:“在中国版的例外论中,中国没有向外输出价值观,而是让别人心向往之。”此外,中国卓越的经济成就是其软实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在过去40年间,中国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令中国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受到其他国家的赞赏。
2019年,奈来华参加奥美集团主办的一场研讨会,间隙谈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助力提升中国软实力,但前提是需要建立起海外品牌形象,提高合规经营水平。而中国企业出海也是全球化智库(CCG)的重要研究领域,在与他共进午餐时,我们就跨国公司形象与国家软实力的相互作用作了进一步交流。
新冠疫情后,人员往来受阻,我们改为线上交流。2020年初我们作为对话嘉宾一起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组织的“疫情与经济”线上研讨会,10月份又一起参加欧洲智库“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主办的线上圆桌会议。
当时为了穿过疫情的阻碍,促进中外交流,全球化智库(CCG)发起“CCG对话全球”视频节目。2021年4月,我邀请他参加对话,讨论“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他十分慷慨地同意了,与我对谈了一个多小时;同年,奈还为我主编的《共识还是冲突? 》(Consensus or Conflict? )一书贡献了一篇“中美之间:展望未来40年”的前瞻性文章。这本书是我和苗绿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的第一部。
在我们对话时,奈再次强调,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仅取决于它怎么说,还取决于它怎么做和它在国内践行自身价值观的方式。他以美国选民投票将特朗普选上总统宝座为例: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加剧了不平等,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受益,其他人则没有。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体系中另一个紧张形势,这激发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许多因全球化失去工作机会的美国人投票支持了特朗普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以“让美国更加伟大”的名义强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虽然他能借此在国内获得更多拥趸,但这种连锁反应让一个国家很难保持自己相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进而削弱自身的软实力。他认为,每个政治领导人都面临着所谓的“双重受众问题”:一重受众是内部的,另一重受众是外部的,有时在内部收效良好的信息在外部则适得其反。鉴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上升,美国和中国都必须慎重对待双重受众问题。
奈长期以来坚持一个观点,即“软实力可以是正和的,双方可以同时受益——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在这次对话中,他又重提“软实力并不必然是零和博弈”,并举例说,“如果中国变得对美国更有吸引力,美国变得对中国更有吸引力,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分歧”,并且,当两国合作,特别是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时,会同时增强中国和美国的软实力。我赞同他的观点。后来,我邀请他向我们推荐一些他自己写就的文章,编辑到我和苗绿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中,他欣然应允,我将这些文章最后辑成一本约瑟夫·奈论述软实力与中美关系的专著。2023年4月,这本《软实力与中美竞合》(Soft Power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分别以中、英文出版,并收录了我与他在2021年4月进行的对话,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对这个问题获得更透彻的了解。
在为此书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奈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演讲,并与我进行了深入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奈提出,软实力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可以合作的一面。如果中美两国彼此吸引,这种吸引力就能成为增强彼此间合作的关键点。而增加人文交流,如更多的留学生、更多的记者、更多游客,都可以增加双方对彼此的吸引、增进了解,在发展软实力的同时增强双方合作的能力。
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全球南方与北方的代表,以及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毋庸置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转折,在特朗普、拜登执政期间,美国进一步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这八年里,双方在贸易上多次交锋。在特朗普任内,中美之间打了三年的关税战。拜登上任后,并没有废除加征的关税,在其任内,美国接连提出“重建更好未来”等倡议,意图在全球发展倡议方面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出台《芯片法案》等法律,意图在科技创新等方面压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还一改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孤立态度”,与盟友联合起来,通过加强五眼联盟、筹划将北约延伸至亚洲、建立“芯片四方联盟”等种种手段,意图对中国施加压力。而2025年,特朗普二度登顶美国总统宝座后,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向全球开打关税战、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新低。
中美竞争下一步将如何演变?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持续崛起,美国将如何应对? 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继续崛起? 美国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顶尖的技术创新国家? 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军备竞赛? 中美之间是否会走向战争?
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许多学者用不同的历史框架来解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称,当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竞争就会不可避免,而历史上大多数“修昔底德”式的案例最后都落入了“陷阱”——战争。我与艾利森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对话和多次交流,并就如何避免让中美两国落入陷阱编著了一本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此书中英文版都已经出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更多信息与思考。
在奈教授看来,中国实力的上升给美国造成了担忧和焦虑,但两国关系并不必然落入“陷阱”。
奈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旗鼓相当的竞争者,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弱点。在评估整体的权力平衡时,奈认为美国至少有五个长期优势。一是地理优势,美国被两大洋和两个友好邻邦包围,而中国与其他14个国家接壤,并与几个国家存在领土争议。二是能源优势,美国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则依赖能源进口。三是,美国的权力来自于其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和美元在国际上的角色。一种可靠的储备货币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自由兑换,以及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法治,而中国缺乏这些。四是人口优势,美国是目前唯一一个预计将在全球人口排名中保持其位置(第三位)的主要发达国家。未来十年,全球十五大经济体中有七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将出现萎缩,但美国的劳动力人口预计将会增加,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4年已经达到顶峰。最后,美国在关键技术(生物、纳米和信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奈认为,崛起大国可以让守成大国感到恐惧,这可能是冲突的根源,但并不绝对。奈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会产生竞争,但不会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除非美国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威胁、双方陷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因此,美国不应夸大中国的威胁,也不要变得过度恐惧。奈认为,双方将在科技(5G、AI、量子计算)、经济(供应链重组、规则制定权)、军事(台海、南海)、价值观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但竞争可以是有益的和良性的,促进自身改善国内的一些问题。而且,竞争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
在《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图书发布会上,奈表示,在当前这个时期,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竞争是存在的,但竞争必须有所节制。双方需确保高层之间有持续的沟通,了解对方的红线,确保事情不会失控,即建立“护栏”机制,不要让脱钩走得太远,特别是在应对大流行病和生态保护等相互依存的领域。奈说,中国和美国都太大了,它们不会对彼此的存在构成威胁,能够摧毁彼此或威胁对方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贸然开战,唱衰对方对双方而言都是危险的。
四
“新冷战”是另一个许多政客和分析人士喜欢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框架。奈认为这是将中国陷于意识形态框架却无视中美两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性挑战。
2023年10月,我邀请奈来华参加CCG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他在会上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精彩演讲。奈再次强调,用“冷战”来比喻中美当前的关系是不恰当的,这会产生误导——中美之间有着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和人文交流,每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几千亿美元,新冠疫情前有大约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这与美苏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此外,中美在生态上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他用21世纪初相隔近20年的两场大流行病为例:在2002—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中美合作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发展,全球死亡人数只有几千人;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美缺乏合作,未能有效阻止疫情扩散,全球死亡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人。这样深刻的教训摆在面前,我们必须认识到,面对跨国危机,大国关系不能只能竞争,也必须要有合作。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威胁甚至超过了战争,通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扩散等传统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等新问题,都需要跨国合作来应对,如果解决不好,全球都要受苦。
奈反驳那些极力主张“脱钩”的人:生态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规律而非政治法则。面对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奈提醒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冷战之类的隐喻,这些隐喻适合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但不一定能准确地描述当下,今日的大国竞争无法沿用20世纪的老套路来处理。他认为:“我们[美中]没有必要卷入一场新的冷战,更不需要卷入一场毁灭性的热战。未来四十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中两国都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情况。美中应该保持‘合作竞争’关系(cooperative rivalry),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忽视。”在为《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他引用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一句话:[美国]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2024年4月,约瑟夫·奈率领阿斯彭学会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出席中美“二轨对话”,回国后,他发表题为《中美合作仍然可期》(US-China Cooperation Remains Possible)的文章,分享了自己在北京参会后的见解,指出中美仍然可以在七个领域探寻开展合作: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核武器,人工智能(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应用),贸易的部分领域,人文交流。活动期间,我将我们为他编纂的《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英文图书赠送给他,他十分高兴,我们一起展示图书并合影留念。
2024年8月,奈邀请我和苗绿参加阿斯彭战略集团的年度安全论坛,我们是当时唯一参会的中方代表。本次论坛围绕“来自中国的挑战”“超越无限:太空与国家安全”“初创企业的救赎:下一代工业基地”“易燃的世界:谁将帮助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 ”“人工智能安全”等主题设置了40余场对话和研讨。在本次论坛上,奈的发言很是中肯,再次表态不赞成中美脱钩。他在发言中指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协力应对全球挑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奈还为自己的最新自传《美国世纪与我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举办了新书推介会,邀请我参加。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他将该书授权给我们翻译成中文,请我们帮他在国内推荐合适的出版社出版,他十分高兴且期待该书能够以中文出版。本书即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中文版面世。
在参加阿斯彭战略集团安全论坛期间,我们还见到了他的太太莫莉,并一起合影。遗憾的是,当年12月他太太就去世了。自他太太去世后,奈身体一直不太好,很少出来参加活动。2025年3月12日,在美国进修的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王子辰专程去拜访他,他对晚辈充满善意、耐心周到,让他挑了一本书赠送给他,并写了赠言。2025年4月下旬我们访美去哈佛大学,遗憾没有见到他。尽管如此,奈教授还是笔耕不辍,时常发表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评论文章。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去世了,实在突然。
五
全球权力平衡变化让美国人非常担忧“山巅之城”将会失去往日荣光。但在奈看来,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带头、当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复兴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地区人口最多,历史上经济也最繁荣。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全球南方国家也必然要求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对发展中国家能否改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环境,即结束“美国世纪”,奈持怀疑态度。奈教授在2024年为报业辛迪加撰写的专栏文章《金砖国家有什么用? 》(What Are the BRICS Good For? )中写道: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内部取得一致仍然有待观察,例如,在金砖国家集团内,俄罗斯、中国、印度都想争夺领导权,避免使用美元,更多以本国货币结算其成员双边贸易的意图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要想真正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中国就必须以深入、灵活的资本市场和法治作为人民币的后盾,而这些条件远未得到满足。因此,在短期内,金砖国家能否成为世界政治的新支点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权力平衡正在呈现多极化的趋势,这与苏联刚刚解体时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化世界格局有很大不同。实力变化必然要求各方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适,这个过程中混乱是难免的。奈教授认为,面对未来,美国应以合作姿态重塑领导力,通过制度与价值观吸引他国追随,在军事和科技领域保持优势,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跨国性挑战与议题上与中国、欧盟等展开合作,因为这些领域唯有合作才能应对。虽然奈坚信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够为全球提供“更美好”的未来,但如果他与全球南方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想必这些美国之外的声音也能够给予他更多启发。
在他的自传《美国世纪与我的一生》中,奈强调,在21世纪,美国世纪并没有结束,但美国的地位将与之前一个世纪大为不同,美国必须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并调整内外政策。奈一再重述他的两个重要观点:“分享权力”和“正和游戏”。他认为,虽然全球化遇到了挫折,但全球将继续保持互联,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合作与接触。在《道德重要吗? 》一书中,他谈到一个国家不能只想着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也必须要考虑分享权力。当前,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极大地改变全球政治,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时,权力成为一个“正和游戏”。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赋权其他国家也有助于本国实现目标。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呼吁美国和中国避免相互妖魔化,并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有吸引力,那么两国之间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减小。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能够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自然会成为“正和关系”的一部分。
我于2008年创办的CCG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我同意奈所说的,“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在此我倡议中国的民间主体,不论是个人、企业、智库和其他组织,都要有促进中外友好的高度意识,了解东西方价值观与文化差异,行走世界时做到相互尊重、谦和自信,从而给外国民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若能更进一步,主动开展“二轨外交”,与西方专家学者和政商界精英进行常态化交流,并与国外机构合办国际论坛或发起新型多边国际组织等,便可以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议题,引领公共舆论,凝聚共识,团结和扩大知华友华人士。这些年来,CCG积极活跃于国际多边场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等并主办分论坛;发起设立“CCG名家对话”节目,与拉里·萨默斯、理查德·哈斯、安格斯·迪顿、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沃尔夫、帕斯卡尔·拉米、约翰·桑顿、马凯硕、托尼·赛奇、尼尔·布什、戴维·兰普顿、斯蒂芬·罗奇、吉姆·奥尼尔等数十位国际意见领袖和专家学者交流观点;2021年CCG又发起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GYLD),旨在构建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国际青年英才对话机制,后获得国家领导人的回信。总之,我们做出的努力让CCG连续多年名列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榜前百强,并成为唯一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上文提到的名家对话实录已经收录在《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一书中,以飨读者。
在自传的结尾,奈这样评估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中国会超越我们,而是权力的分散会产生熵,导致一种无序的存在。更令他担忧的是美国的国内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对美国的软实力和美国世纪的未来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外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也可能在内部失去美德和对他国的吸引力。”例如,在他看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背叛,退出多边机制、蔑视盟友、煽动民粹,不仅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还加速了全球秩序的碎片化。他认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软实力,并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将美国“推向孤立”。他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美国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景对世界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
直到去世前,奈一直都在关注和分析美国新政府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忧心忡忡,但他还是保持了乐观态度:尽管美国存在种种缺陷,但它还是一个创新型社会,过去曾经成功自我更新和重塑,也许Z世代能再次做到这一点;“……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爱和一缕微弱的谨慎乐观情绪留给他们”。
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曲折前行。当前的历史性大变局下,旧有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深刻调整,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将面临许多挑战,不管中美两国在其间发挥何种作用,有一个问题确凿无疑:技术和环境领域的挑战需要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远超过战争带来的破坏规模,而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也并非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好消息是中美在2025年5月10日—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经贸高层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中美之间:展望未来四十年》一文中,奈在结尾写道:“未来在到来之前有无限可能性。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并没有被封印。”我想这句话正适合用来展望我们正在变化的世界,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与行动。
文章选自《全球化研究(2025秋季卷)》2026年1月12日
-相关链接-
王辉耀:探索全球权力的性质和变化——纪念“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最新力作《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在CCG发布
CCG发布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新著《软实力与中美竞合》